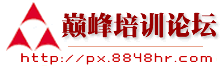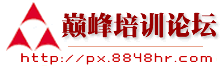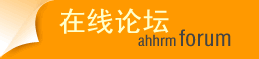| 牛人 |
|
|
| 等級:論壇騎士(三級) |
| 積分:7010分 |
| 注冊:2006-8-14 |
| 發貼:2201(1215主題貼) |
| 登錄:3776 |
|
|
| 2019中國勞動力市場發展報告|未來社會人的意義在哪里? |
2019中國勞動力市場發展報告:2020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將達到874萬人,同比增加40萬人,畢業生人數再創新高,就業形勢依舊嚴峻。報告顯示,不少理工科學校以及綜合性大學的理工科專業的“就業成績單”十分亮眼,而文科畢業生就業困難。
《2019中國勞動力市場發展報告》指出,大學生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外部環境變化造成大學生需求升級、大學生供給調整滯后,具體表現為文科畢業生就業困難,理工科人才短缺。
針對理工科人才的“結構性短缺”, 北京科技大學招生就業處副處長劉曉杰表示,這和目前國家創新發展過程中廣大用人單位急需核心技術領域的人才需求基本一致。同時,一些傳統意義上財經類、管理類的用人崗位,目前也出現了對工科學生的大量需求,也確實客觀地反映出市場對理工科人才的需求迫切。
……
人機共生還是替代吞噬:如何讓人在未來活出“人”的樣子?
在最近兩個世紀進步主義思潮的照耀之下,人們相信,是知識的進步推動了工業革命、生產力革命和管理革命,將人類帶入現代社會。也因此,當AI、當物聯網、當人機共生初現端倪時,人們也禁不住歡呼,似乎一個全新的酷炫的未來就在前方不遠處閃耀。
可事情真的如此簡單么?
1月8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BiMBA商學院院長、北京大學未來教育管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春花在“2020未來教育論壇”上,推演了人機共生時代的幾種可能:機器或者知識幫助人機之間產生更多的可能性,我們稱之為人機共生;但也可能機器幫助了人之后,會有一個偏離共生;也很有可能,在機器出現在這個世界當中的時候,僅僅是機器發展,對人也許是傷害,偏害共生;還有一種可能是我們無法想象的,替代吞噬。
換言之,在未來人機共生的社會中,人的意義在哪里?如何讓人能夠在未來活出“人”的樣子?
以下為正文:
在我整個研究過程當中,給我很大啟發、也使得我不得不去討論的一個話題,那就是知識在起的作用。
我們會發現有一個變化,以前我們會認為很多東西可能是在“道”的層面,它很難降到“器”的層面;在過去的理解當中,我們也會認為形而上、形而下是分開的。可是隨著技術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我們會發現兩者之間沒有辦法有界限,所以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我們突然間意識到,“道”與“器”之間必須完全融合。所以,在德魯克看,過去的150年,真正推動社會變革的其實是知識。
他在下這個結論的時候,把過去的150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中,他說當知識可以變成我們稱之為工具的時候,就會發現整個知識的傳遞改變了整個世界,也就是工業革命的出現。在這之前需要的都是經驗,但是經驗很難大面積復制和普及,所以當它可以被印刷、當經驗可以變成知識、變成非常普及性的東西的時候,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提高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整個工業革命真正的起步,不在于機器,而在于知識變成了機器和工具。
第二個階段,管理革命的真正出現其實是來源于知識變成了生產的過程,也就是當知識應用于整個生產過程的時候,才會有大量我們稱之為生產力革命的出現,也就是生產效率的出現。整個生產效率的提高,就導致了整個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
第三個階段,德魯克稱之為“知識被運用于知識本身”——他定義為管理革命。而在管理革命中一個最重要的變化是什么?就是讓體力勞動者變成知識工作者,而所有人成為知識工作者的時候,整個社會的效率和社會的發展就完全不一樣了。
如果沿著這個邏輯往下走,就會發現,今天有一個更大的變化:不僅僅是知識應用于工具,知識應用于生產力,知識應用于知識本身,知識還出現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知識應用于系統創新。
所以我們就來到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時代我們今天用了一個詞描述它,叫“人機共生”。回顧最近150年,知識變成社會根本變革的力量,走到今天,知識變成了創造未來社會的力量。你不僅僅看到知識變革這個社會,而必須去理解知識本身開始創造社會。
所以,當我們的研究回到人機這個概念的時候,會發現出現了四種可能性:機器或者知識幫助人機之間產生更多的可能性,我們稱之為人機共生;但也可能機器幫助了人之后,我們會有一個偏離共生;也很有可能,在機器出現在這個世界當中的時候,僅僅是機器發展,對人也許是傷害,我們叫做偏害共生;還有一種可能是我們無法想象的,叫做替代吞噬。
我們在討論這個概念的時候,其實很需要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未來社會不僅僅有人,還有一個更大的可能性,是人跟知識組合之后的一個社會。在未來,人機共生的社會中,人的意義在哪里?如何讓人能夠在未來活出人的樣子?這實際上是我們今天的教育可能遇到的最大的挑戰。
如果我們按照這樣的一個概念去看,會發現知識半衰期實際上變得越來越短。我在過去的課程中跟很多人討論,管理學的知識有效時間大概可以多長呢?我們開玩笑說,以前的管理學知識可能兩年有效,但是今天的管理學知識,好像入學三個星期之后很多東西都變了。所以,我們會發現,技術帶來社會進步的速度其實是超過我們想象的。你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今天的教育、我們在知識學習上面臨如此巨大的挑戰,是因為它變化和衰退的時間周期的的確確超過了我們的想象。
對于知識本身來講,需要承擔兩個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如何全面地去真正理解知識,因為知識已經不再是一個變革的要素了,它本身就在創造社會,我們需要認真地理解,我們是不是真的理解知識;二是,因為知識是在創造社會,所以我們必須對整個星球、整個宇宙要承擔責任,因為你在創造它。
所以我們會要求,無論是從教育還是一個人的維度上來講,我們可能肩負著兩個最大的、之前可能沒有意識到的巨大的責任,一個就是你在創造一個社會,一個就是你對整個宇宙必須責任承擔。對我們來講,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致力于去創造知識。
那如何致力于創造知識?我想到非常多的東西。首先想到的就是,作為一個主體,我們能不能真正地覺悟。人機共生之后,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是完全改變的,不再是從屬關系。如果每一個都是主體的話,那作為其中最重要的主體“人”來說,你的主體意識如何覺醒?你如何意識到你的責任,如何意識到你對周遭世界的影響,甚至對于整個宇宙的影響。所以我會想到蘇格拉底,他會告訴你,當你覺得你無知的時候,其實才是你獲取知識的真正前提。所以林校長講五個教育共識的時候,也會告訴我們,我們如何真正擁有批判的精神,我們如何真正理解我們跟這個世界的關系。而這種主體的覺醒、主體的覺悟,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通過教育去喚醒。
第二,我們有沒有能力去超越感知?我們看到的就是真的嗎?我們沒有看到的就不存在嗎?其實我過去在學習的時候,感受最深的一個概念叫做洞穴理念,當柏拉圖討論這個概念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我們其實是受限于我們的認知,我們就會認為我們看到的是真實的,我們理解的才是存在的,我們存在的才是合理的。可是如果你沒有能力去超越這些感知,你沒有能力去認知那些永恒存在的東西,那也許你就不理解什么叫做知識。所以當我自己不斷去研究的時候,我深受它的影響。我們知道知識有一個能力,這個能力就是超越于有形去感知完全未知的東西。所以當我們看未來教育的時候,其實我內心最想感受的東西,就是我們有沒有能力讓學生不是以已知理解未知,而是有沒有以未知創造未知,這是我們超越感知最重要的部分。
第三,我們能不能高于自我。我們在很多時候,其實都不斷地去理解我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如果從《道德經》看,有老子的啟發,他就會告訴你為什么開篇叫“道可道,非常道”,就是因為他告訴你這個道并不是恒定的。為什么人與自然界之間的認知當中,我們一定是有能力跟它組合在一個空間當中,是因為這個道并不是一個恒定的道。如果你愿意去跟這個自然做融合,高于你自己的追求和自己的想法,把你完全放在一個大的空間當中,你的選擇、你的行動,以及你的努力,其實就會是一個新的道。這種重新去設立的道路,重新去建立空間,正是《道德經》給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啟示。
而這種啟示就意味著,我們在教育和知識的場景當中,我們是有能力為我們的學生、為我們自己去創設一個新的場景,而這個場景經你的選擇、你的努力,以及你的行動,會是一條新路。
如果我們認為,知識在未來是一個完全創造社會、完全創造世界的一個最重要的核心變量,那么重要的事情在于,我們能不能夠高于自我、能不能夠超越感知、能不能主體覺悟。我覺得這三樣東西完全要由教育去承擔它。
我一直在想,我們人類是在什么時候開始知道自己的。我們就會回到那個時間,那個時間是《荷馬史詩》,那是人類與神可以對話的時代,也是人與自然可以共存的時代。那個時代中你會發現,人對自我的認知與對世界的認知都是非常篤定、非常純粹,也是非常美的。
經歷了1400多年,我們來到了一個讓我們都覺得非常殘酷、夢幻,卻又無力撕扯和掙扎的地方,就有了但丁和但丁的《神曲》。
我們又繼續再走接近500年,我們又會看到了人類再一次想我怎么樣去從現實和脫離現實之間找一條路,就有了《浮士德》,有了歌德。當歌德和《浮士德》出現在我們身邊的時候,就發現我們每個人厭倦的知識,想回到現實。但是回到現實的時候又非常的失望,最后《浮士德》說他想回到希臘。他為什么會想回到希臘,回到《荷馬史詩》的時候?是因為這時候人類終于理解了什么叫人、什么叫自然、什么叫神。所以當我們不斷追溯人對自身認識的時候,我們來到了米利都學派,他告訴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萬物的本源是什么,當人類在這個時間清楚地知道他跟世界的關系的時候,他最重要的武器是什么?是純粹的邏輯尋求了事物的本質,這是智者,人類脫離了混沌。
我想,如果我們面向未來,也許這是一條重要的路,也就是我們知道自然,我們知道世界,我們也回顧自己,也知道事物的本質是什么。而這一切恰恰就是今天需要再教育和我們自己所要探索的路。
最后一句話,也是我個人最近常說的一句話:其實我們真的不擔心機器像人一樣的思考,我們最擔心的是人像機器一樣的思考。未來教育也許最重要的是,恢復人自己認知的覺醒。
(本文部分為北京大學教授陳春花,1月8日在2020未來教育論壇的演講) |
|